大唐咸通十二年的秋天,一辆囚车缓缓驶过喧闹的长安街市。秋风萧瑟,片片落叶盘旋着平地而起,不甘心地飞向枝头、飞向天空,最后却只能被熙熙攘攘的人群踩在脚下,徒留一声枯萎的叹息。
人群跟着囚车缓缓移动,斥骂声与叹惋声混成一片。
女人们骂:“臭不要脸的狐狸精,到处勾引男人,早就该死了!”“就是,把我家男人勾得魂儿都没了!”“我家那老不死的把房子都卖了,巴巴地跑去给这骚狐狸送钱!”“什么才华,都是狗屁!”……
男人们叹:“真是可惜了这才貌双全的姑娘,竟要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官府办事,真是一点情面也不讲啊!”“还讲什么情面?这分明就是公报私仇,谁不晓得呀!”“可惜了啊!”……
而囚车中的女子却神情淡然,仿佛将要赴死的是别人一般。她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着,希望能最后看一眼那张熟悉的面庞,心中默默念着:飞卿,飞卿,你来了吗?
十岁那年,鱼幼薇在家乡鄠杜第一次见到诗名满京华的温庭筠(字飞卿)。他特意为她而来,因为他听说下邽出了个能出口成章的神童,便奔赴下邽去寻她,不想扑了个空——鱼幼薇已经返回了在鄠杜的老家。于是他又风尘仆仆地赶到鄠杜,终于得以相见。
彼时鱼幼薇虽然年仅十岁,但举手投足间已有一段少女风韵,明眸皓齿,唇若施脂。而温庭筠却是人老面丑,作揖微笑时,眼角便堆满了褶子,犹如秋风中惨淡飘零的枯叶。看着眼前这个兰花一般的小女孩,温庭筠竟有些自惭形秽。
不过,鱼幼薇早就听说过温庭筠的才名,对他的到来更是惊喜万分,丝毫没有介意他的相貌。她压制着内心的狂喜盈盈一拜,轻启朱唇道:“先生大驾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只是小女子何德何能,竟劳先生大驾!”
十岁的她尽量装出大人的样子,但在温庭筠看来却是满满的稚气。他回礼道:“幼薇多礼了,听闻坊间流传着幼薇的几首诗作,皆是妙语佳句,想不到幼薇小小年纪,竟有这等造诣!”
“在先生面前,小女子那几首拙作都算不得诗了,”小姑娘面露羞涩,但掩不住心中的喜悦,“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小女子斗胆,不知能否求先生赐下墨宝?”
温庭筠欣然同意,于是挥笔写下了《题鄠杜郊居》,而鱼幼薇则作《卖残牡丹》回赠。温庭筠爱才惜才,他主动来找鱼幼薇,不仅仅是出于好奇,更是做好了收徒的准备。这次会面后,他便正式收下了鱼幼薇这个女学生,并时常为她指点。
那一年温庭筠42岁,整整大了她32岁。鱼幼薇的父亲是一名屡试不第的读书人,她虽是女孩儿,却在父亲授意下学了很多诗词歌赋。父亲去世后,她从下邽回到鄠杜,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帮青楼的姑娘们浆洗衣物来赚取生活费用,日子很是难熬。温庭筠的出现给了她莫大的安全感,这个面貌丑陋的中年男人,让她重新找到了父亲的温暖。他在精神世界中指引着她,也在物质世界里援助了她。十岁的女孩子正是身体与心灵迅速成长的时期,她愈发出落得亭亭玉立,而他愈发苍老丑陋,两个人站在一起莫说像父女,说是祖孙只怕都不会有人怀疑。
每次来看望鱼幼薇,温庭筠都会带一些上好的衣料和胭脂水粉。他非常钟爱这名女弟子,只要看着她如同兰花一般袅袅娜娜地长成少女,然后嫁个好人家,便觉心满意足。
十四岁那年的春天,长安城草长莺飞,温庭筠携鱼幼薇及几位好友同游乐游原,大家对着万丈春色把酒言欢,吟诗作赋。其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公子,名李亿,字子安,生得风流倜傥,气度不凡。席间,温庭筠故意让李亿和鱼幼薇邻座,而鱼幼薇却固执地挨着温庭筠坐下,流转的目光中是无尽的情思。
“幼薇姑娘真是才貌双全,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李亿温文尔雅。
“李公子过奖了,听闻李公子即将应试,想来定能高中,日后做了大官,不要忘了我们这些布衣之交才是。”鱼幼薇俏皮道。
众人哈哈大笑,李亿笑道:“怎敢怎敢,若真是托了幼薇姑娘吉言做了官,只希望能娶个像姑娘这般才貌双全的女子为妻,才不负此生了。”
不等鱼幼薇说话,同将应试的裴澄便道:“妻就算了,妾还差不多,子安这是忘了家里的母老虎了?”他一面说,一面学着老虎的样子张开十指。裴澄虽然也生得眉目清秀,但微吊的眼梢总是带了些狠戾,配上这样的动作,倒真有些老虎的风范。
众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人接道:“就是,子安兄忘了上回回家晚了吃闭门羹的事儿了?”
“不过嘛,在下倒是尚未婚娶,幼薇姑娘若是不嫌弃……”裴澄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看着鱼幼薇道。
“你还要不要脸了,这京城里谁不知你裴郎天天眠花宿柳,杏花院的门槛都快让你踏平了,谁家姑娘愿意嫁给你?”不等裴澄说完,便有人笑骂起来,大家闻言又是一番哄笑。
鱼幼薇抿嘴一笑,偷眼看向温庭筠,双手不自觉地扣紧了他的胳膊。
席散后,温庭筠送鱼幼薇回家。日近黄昏,暖暖的阳光摊在碧草上,初开的蓓蕾也披上了一层金光。马车里,温庭筠心事重重的样子,鱼幼薇忍不住问道:“先生有心事?”
“没……其实也算吧,幼薇啊,”温庭筠向来直言直语,刚刚和朋友们在一起还谈笑风生,现在却吞吞吐吐起来,良久,才缓缓道:“你年纪也不小了,是时候说门亲事了。”
“先生,我不想嫁人。”鱼幼薇斩钉截铁地道。
“早晚要嫁的。你看刚才那位李公子怎么样?”原来是有意撮合他们,难怪他刚刚想让鱼幼薇坐在李亿旁边。
“幼薇自知出身贫寒,能嫁给李公子做妾室已是高攀了,但是……”她“但是”了半天,还是没说出后半句,脸颊却红得像天边燃烧的彩霞。
温庭筠猜出了大半,“幼薇……有心上人了?”
“嗯。”她羞涩地低头,长长的眼睫垂下来,从面颊到耳朵到脖子都红了个透彻。
“怎么不早说?那是谁家公子,为师看看能不能去做个媒人。”
然而凭他怎么问,鱼幼薇就是不肯说。看着她的神情,温庭筠心里敏感地闪过一个念头:“该不会是我吧?”但随即又在心里痛斥了自己一番:“你老得都快能做幼薇的爷爷了,竟然还冒出这种想法,岂非禽兽!”
鱼幼薇不肯说,两人之间的氛围忽然有些尴尬。快到家时,鱼幼薇终于打破了沉默:“先生,既然我就快成年了,能不能请您赐个字呢?”
温庭筠思索了一番。他想起了第一次见到鱼幼薇时的场景,对她的第一印象,便是一朵袅娜的兰花,这几年,这朵兰花更是在自己眼中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思忖须臾,他缓缓道:“幼薇秀外慧中,取字‘蕙兰’吧。”
没过多久,幼薇及笄,字“蕙兰”,成年礼刚过,上门提亲的人便踏破了她家门槛。不过,来提亲的世家大户无一例外地都想娶她做不知第多少房的小妾,至于要娶她做正妻的,要么是五大三粗的屠夫,要么是尖嘴猴腮的小贩,没一个能入得她眼的。有些被拒绝的媒婆走到门口,还不忘扭头啐一口:“呸,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都穷成什么样了,还指望着攀什么高枝儿呢!真把自己当蔡文姬啦!”
科举放榜后,鱼幼薇去温庭筠家里。每次科举,温庭筠都会参加,但总是落第。这一次,温庭筠和李亿同去考试,她倒不关心他们能不能考得中,只是这么久不见先生,心中思念而已。
刚到温庭筠家门口,便见温庭筠的儿子温宪慌慌张张跑出来,鱼幼薇赶紧问他出了什么事。
温宪脸上的神情极其复杂,既有焦虑,又有紧张,还带着许多羞愧,吞吞吐吐地道:“家父……唉!他,他科场舞弊,被下狱了!”说完便急忙忙跑了,大概是求救去了。
鱼幼薇听罢呆愣了许久,好半天才缓过神来。科场舞弊?被下狱?怎么会出这种事!在她的印象中,温先生一直是光明磊落的,即便屡试不第,也决不会做那种下作的事情。温庭筠对自己恩重如山,如今他出了事情,她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但是她一个弱女子,能求助于谁呢?思来想去,她脑海中浮现一个名字:李子安。
去往李家的路上,一大群人簇拥着跨马游街的新科状元,锣鼓喧天,好不威风。不过,她没心情去关心那些,挤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赶紧去李家了。李家颇为显赫,大门前有两尊石狮子,石狮子上还挂着红绸花,府邸门口热闹非凡,来来往往的人都在道贺,有一位管家模样的老先生在门口迎客。
看来,李亿这是中了新科进士了。不过,她并没有看到李亿的身影,正寻索间,忽听得人群中一声喊:“新科状元回来啦!”
人群像潮水般向两边退开,将中间的路空了出来,旋即,便见一位身着状元服的英俊男子骑马而来,至府门前下了马,见大家纷纷道贺,满面春风地向众人抱拳还礼。
正是李亿,原来刚刚跨马游街的新科状元是他!
李亿一眼便看到了人群中那张带着焦虑与讶异的俏丽面庞,与大家还礼后径直向她走来。
“想不到幼薇姑娘也来了,真是幸甚,幸甚!”看到她,李亿满眼满心都是欢喜。
“恭喜李公子了!幼薇前来,还想问一下温先生……”
不等鱼幼薇说完,人群中便有人打断了她的话:“姑娘不知道吗?温先生在考场上抄袭被抓个正着,已经被下狱了!”
李亿赶紧解释道:“不是抄袭,温先生是帮别人写文章被发现了,温先生学富五车,八叉手即成一韵,怎么可能去抄袭别人的?”
原来是这样。但不管是谁抄谁的,下狱是真的。
“幼薇姑娘是想救人吧,你放心,我已经找人去打点了,但是结果如何,还要看官府裁决。”李亿一边说,一边伸出手,似乎想拍拍她的肩膀,但刚伸到一半,鱼幼薇便退了一步道:“多谢李公子仗义相助,那幼薇先行告辞了。”
李亿那只悬空的手僵了片刻,便讪讪地缩了回来。
一个月后,终于获释的温庭筠来找鱼幼薇。这一次,他是来道别的。
“京城我怕是没有立足之地了,明天我去江陵,或许还能谋份差事。”温庭筠神色黯然。
鱼幼薇尽量压制着心底的难过,缓缓道:“先生,此一别,不知何时回来。”
“不好说,可能很快就回来,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再也不回来了。京城,是他曾经多么憧憬的地方,经年蹉跎,却只落了满身满心的伤。
“先生,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帮别人写文章呢?”鱼幼薇终于道出了心中的迷惑。
温庭筠嘴角闪过一抹冷笑,眼中尽是桀骜,“幼薇,你知道今年一共录取了多少个新科进士吗?”
“除了那个先生帮忙的,还有三十个吧。”
温庭筠不屑地“哼”了一声,“这三十个人里,还有六个人的文章也是出自我手。哈哈哈哈!”
鱼幼薇惊呆了,看着先生得意大笑的样子,忽然明了。这些年每逢科考,温庭筠都会前去,他早就知道自己不会被录取,不是因为才华不济,而是因为他是温庭筠,是得罪过考官、在官场里早已被恶名加身的温庭筠。他在考场上帮别人写文章,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而已。既然不得认可,那就用这种方式来讽刺黑暗的官场吧。
“对了幼薇,子安前程大好,人也不错,虽说嫁给他只能做二房,但也好过嫁给那些只能做七房八房的。”温庭筠又把这件事提起来,大概是想在自己离开之前先把鱼幼薇的终身大事安排妥当。
“如果幼薇真的有心上人了,就告诉我,能安排的我一定尽力安排。”温庭筠似乎想起了上次在马车里鱼幼薇说了一半的话。
“先生果真想知道?”她的长睫忽闪着,一抹红霞又飞上了面颊。
“当然啊!”温庭筠有些着急。
“我前几天绣了个荷包,送给先生的。”鱼幼薇话锋一转,还是没有回答,竟是拿出一个荷包来,自顾自地系在温庭筠腰间。一双纤纤玉手无比灵动,看得温庭筠有些痴了。
“荷包里的东西,先生明天在路上看吧,看完就知道了。”鱼幼薇低头道,面上红霞已经染到脖颈。
温庭筠不明就里,他哪里会等到明天?刚离开鱼幼薇家,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荷包,里面只有一颗精致玲珑的骰子。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那是他前几年写过的诗句。骰子骨质,内嵌相思红豆,故曰“入骨相思”。
温庭筠呆愣半晌方如梦初醒。原来幼薇的心上人,真的是自己。那一刻他不知道自己心里是苦涩还是甜蜜,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妙龄女子竟会倾心于他这个年过不惑又其貌不扬的小糟老头子,如果是个不认识的姑娘,他一定会为自己的宝刀未老魅力无穷而兴奋不已,但偏偏这个姑娘,是他悉心培养了好几年的女弟子。他早有家室,虽然妻子已经去世,但他早就习惯了这种自在的单身汉的生活,闲时逛逛青楼,与风尘女子们调笑一番,亦或一夜温存,付了钱也就两不相欠。女子的青春还不就是那么几年,若是荒废了,便是终生的遗憾。他当然不会坐视幼薇误入歧途,早就过够了颠沛流离、衣食无着的日子,他只希望,幼薇能嫁一个年岁、相貌、脾性相当的如意郎君,一辈子锦衣玉食,不要像他一样潦倒。
温庭筠到了江陵后,鱼幼薇的信一封接一封地寄来——也不知道她在哪里打探到了他的地址,每一封,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极尽缱绻。不过,他只是将那些信笺珍藏起来,从不回复。
李亿高中状元后,任官补阙,可谓前程大好。温庭筠去江陵之前曾找过他,拜托他照顾鱼幼薇母女二人。李亿果然不负所托,隔三差五地便来看一看,有时候自己抽不开身,便派人来送些钱粮接济一下。李亿温文尔雅,鱼幼薇虽然谈不上有多喜欢他,却也不反感。只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她心中已经装了一个人,便再也容不得他人,即便他们之间缘分渺茫。
冬去春来,一年的时光倏忽而过,在鱼幼薇写了很多石沉大海的信后,终于收到了回信——一封劝嫁的回信。几乎同时,李亿请的媒人也上门提亲了。
那一天鱼幼薇站在屏风后面,听着母亲与媒人的话。母亲道谢时,媒人道:“老身只是挂个虚名儿,温先生才是真正的媒人呐!这桩良缘,都是温先生一力促成的!”
两行清泪顺着脸颊缓缓流下。温先生,是她从小便敬仰的人,是她十岁那年有幸拜得的恩师,是她这几年成长岁月中的知己,更是她的心上人。或许是他的出现弥补了她过早缺失的父爱,或许是为他的才华所折服,又或许仅仅因为他是他。有时候,爱情这种东西总是来得毫无征兆,又毫无道理。如果他一定要她嫁给李亿,那么,她嫁。
数日后,鱼幼薇穿上大红的嫁衣乘着花轿来到了李府。李亿爱惜她的才貌,对她格外宠爱。然而这份宠爱没有持续多久,便引发了李府一场又一场的家庭风波。李亿妻子裴氏隔三差五便要吵骂一番,鱼幼薇何曾见过这等阵仗,只能忍气吞声。
这样鸡飞狗跳的日子挨了半年多,鱼幼薇终于不堪忍受回了娘家,打算能躲一天是一天。母亲正在洗衣服——那些青楼女子的衣服,赚点钱来糊口。
当初嫁到李家,鱼幼薇本打算让母亲一同搬过去,但是母亲不肯。后来想想,幸亏没有同去,不然裴氏不知还要怎么闹腾。每次她接济母亲总是小心翼翼的,有一次被裴氏发现,难听的话骂了一箩筐。
回娘家才知,母亲近来身体不好,总是咳嗽不停,痰中还隐隐带着血丝。鱼幼薇带了一名丫鬟,名唤绿翘,聪明伶俐,见老夫人在洗衣服,赶紧过去帮忙。
“娘,家里吃穿都有,我供养着您就行,以后别再接这种活儿了。”鱼幼薇拿过手帕给母亲擦手,水葱一样的手指抚过母亲长满老茧的手掌,她心疼不已。
“我呀闲不住,能干活就干点,总不能一天到晚都闲着。”每次鱼幼薇劝说母亲,母亲都拿这句话搪塞。
母女俩正说着,外面忽然有一辆豪华的马车停在了门口,一个穿金戴银的女人气势汹汹地下了马车,在一众丫鬟婆子的簇拥下杀进房来。
“好你个吃里扒外的小娼妇!还会偷东西了,还偷到老娘头上来!回娘家?我看是想转移赃物吧!”裴氏对鱼幼薇,只要一开口,准没好话。
“这话说得好没道理,我何曾偷过什么东西?”饶是鱼幼薇脾气再好,也受不得这样的栽赃。
“夫人,幼薇只是回来看看我这把老骨头,她是我看着长大的,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她不可能做的。”鱼幼薇母亲早就听说裴氏泼辣,但从未听女儿说起,还以为她们就算相处不好,也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不至于闹僵,万没想到,裴氏竟然会追打到家里来。
“放屁!就是你这个老娼妇养出来的小娼妇,母女俩一个穷酸样!哟,这是什么?杏花院那些骚货的衣服吧?哈,难怪这么会勾引男人,原是打小调教出来的,也不知道在那种地方待了多久,让我家那个不长眼睛的给娶进门了!”裴氏一边说,一边向那些衣服里狠狠啐了两口。
鱼幼薇气得杏眼圆睁,肩膀颤抖不已,已然说不出话来。绿翘在一旁赶紧打圆场:“夫人莫要动怒,别是有什么误会,还不知夫人丢了什么,不如说出来,我们也能帮着找一找。”
“还用你们找吗?给我搜!”裴氏说完,随身带的几个丫鬟婆子便一拥而上,把房间里翻了个底朝天,什么瓶瓶罐罐、衣被箱箧摔了一地,最后在鱼幼薇刚刚带回的小包袱里翻出了一只小小的金步摇。
那只金步摇的确是裴氏的,究竟是什么时候跑到了鱼幼薇的包袱里,她也不知道。遑论过程如何,结果总归是“人赃并获”,虽然李亿说尽好话,裴氏还是容不得鱼幼薇,坚决将鱼幼薇送到道观去。裴氏出身世家大族,李亿能高中状元,也多亏了岳丈家的极力推荐。因此,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得罪妻子,最后只能忍痛割爱,让鱼幼薇离开李家。
什么山盟海誓、情比金坚,还不到一年,便在现实的凄风苦雨中草草收场。临行前,李亿深情款款地说道:“你要等我,我一定会接你回来的。”他那样说,仿佛只是为了挽回一点面子。鱼幼薇摇头叹息,泪在眼中,当着他面却始终执拗地不肯落下,直到转身的那一刻,泪水才决堤了一般汹涌而下。鱼幼薇入咸宜观不久,李亿便携家人去外地为官了,而那句“我一定会接你回来的”自然也成了永远不可能兑现的诺言。
咸宜观,一豆孤灯,一捧黄卷,一身素净道袍。她提笔写道: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从此鱼幼薇已死,活在这世上的,是放浪形骸的女冠鱼玄机。
第二天,咸宜观门外贴出了一张告示:鱼玄机诗文候教。
长安城那些有点墨水的纨绔子弟们蜂拥而至,打着“切磋诗文”的幌子来和鱼玄机聊天扯皮,有时候在桌下假装不小心碰碰她的脚,甚至偷偷捏捏她的腿,而鱼玄机竟也不介怀,依旧侃侃而谈。
有个别大胆的孟浪少年便试着再进一步,假装酒醉行动不便,提出夜宿观中的请求。有那相貌丑陋或不通文墨的都被鱼玄机直接赶了出去,而相貌清秀、文雅多才的男子竟真的得了手。当然,事后也总要留下些玉佩之类的物什。从此一传十、十传百,休说长安城的青年才俊,就连外地的读书人也都巴不得来咸宜观一睹鱼玄机风采,若再能得一夜温存,更是三生有幸。
远在江陵的温庭筠得知鱼幼薇的变故先是震惊,而后是愤怒。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曾经悉心培养的女弟子,竟沦落到这等地步,这与那些迎来送往的青楼女子有和区别!
于是温庭筠修书一封,劝说鱼幼薇回归正途。然而那封信竟是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想起鱼幼薇曾经写给自己的那些信,想起她曾经对自己抱着怎样的幻想与痴念,在写了那么多封石沉大海的信后,却等来了一封劝嫁的信,那一刻的她,该是怎样的绝望。
温庭筠提笔,写了一阕《望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如果当时他没有撮合鱼幼薇和李亿,鱼幼薇也不至于入道观,更不至于性情大变。
他决定回去看看,面对面地与她谈一谈。
在温庭筠从江陵赶回长安的时候,拜倒在鱼玄机道袍下的青年才俊又多了一批,其中有两人非常出色,一为陈韪,一为裴澄。
当她还是鱼幼薇的时候,曾和温庭筠一起参加一些聚会,席间见过几次裴澄。那时裴澄便有心接近她,但后来她在温庭筠的撮合下嫁给了李亿,心里的小小幻想也就破灭了,不想李亿竟舍她而去,裴澄知道后兴奋不已,忙不迭地借着“切磋诗文”的名义来找鱼玄机,但鱼玄机对他非常冷淡,裴澄有些莫名其妙。
这一日,咸宜观中又聚集了十来名读书人,丫鬟绿翘也随侍在侧。对于鱼玄机来说,绿翘大概是她最大的安慰了,在她入咸宜观的时候,绿翘主动提出陪她同往。闲暇时,她便指点绿翘读书写诗,绿翘聪明伶俐,很快便得了她真传,成了不折不扣的小才女。那些孟浪子弟除了来看鱼玄机,还有一部分人也惦记着绿翘。
“昨天刚下了场大雨,咱们就以‘雨’为题联句吧!”鱼玄机提议。
“真是巧了,我也正想说呢!”陈韪笑呵呵地道,“那谁来起个头呢?”
“裴兄刚升任司法参军,正是可喜可贺,不如由裴兄来起个头?”大家一起看向裴澄。
裴澄一直受鱼玄机冷遇,总想表现一番,便也不客气,道:“那我就献丑了!”略一沉思,又道:“雨落惊鸿起!”
“一瞥念别离。落花湿金诺,”
“且慢!”陈韪的“诺”字音未落地,就被鱼玄机打断了。“‘雨落’和‘惊鸿’有什么关系呢?再说都眼见着下雨了,大雁还飞什么?大雁疯了吗?”说罢还不忘轻蔑地笑一声,大家听了纷纷附和,继而哄笑。其实“雨落惊鸿起”本没什么毛病,大雁在雨中飞也是有的,鱼玄机明显就是想找茬奚落他一番,而其他人基本都是唯鱼玄机马首是瞻,就算她说“昨天分明下了一场雪而不是雨”,大家也会跟风附和。
“鱼玄机,你三番五次针对我,有意思吗?”长久以来压制在心底的疑问与愤怒终于爆发了。
“你觉得没意思的话,就滚啊,为什么还要来呢!”鱼玄机反唇相讥,泼辣气质颇有几分裴氏的风采。
“就是就是,明知道人家不喜欢,还跑来献什么殷勤!”有人小声嘀咕,也不知道是怕裴澄听见,还是故意的想让他听见。
裴澄终于忍无可忍,拂袖而去。鱼玄机大笑着,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眼角眉梢透着一股狠戾,她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桌子上,道:“姓裴的没一个好东西!”众人了然,她大概是因为之前受尽裴氏欺凌,而迁怒于同样姓裴的裴澄了,大家不免心里有些为裴澄叫冤,但没有人敢说出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联句、行令。
这些天陈韪几乎天天留宿观中,这个颇有才华的男子面貌俊朗,身材颀长,很得鱼玄机的赏爱。这一日散席后,鱼玄机心里闷闷的,便不让别人陪同,自己一个人去乐游原走了走。转眼经年,物是人非,想到曾经温先生经常带她来此间游玩,又想到联句时他们说的“雨落惊鸿起,一瞥念别离。落花湿金诺”句,不禁更加心神黯然。又近黄昏,她对着沉沉欲坠的斜阳道:“风尘误佳期。”竟是自行联了一句,她有些后悔当时的懦弱,如果她再勇敢一些,死缠烂打地跟着温先生,坚决不嫁入李家,那么现在会是怎样的结局?
回答她的只有夹杂着青草气息的微风,犹如一声无奈的叹息。
回来时路过一个胡饼铺子,便顺手买了两张胡饼,她记得绿翘最喜欢这个。这几年,多亏了绿翘一直在她身边,令她深感欣慰。回到咸宜观已经快宵禁了,她没去自己房中,而是径直去了绿翘房间。
刚要举手敲门,却听见房中一阵阵女子紊乱的娇喘,还有男子粗重的气息。
“那个夜叉要是知道了,还不杀了你!”陈韪的声音。
那声音在鱼玄机听来,犹如五雷轰顶。“夜叉”是谁?她吗?
“那怎么可能让她知道!裴夫人再三交代过,放了金步摇的那个包袱一定要让她自己拿着,我只给她拿其他的粗重物件,要不然她怎么能不怀疑我!”绿翘的声音。鱼玄机想起当年那支莫名其妙的出现在自己包袱里的金步摇,这才恍然大悟,气得浑身颤抖不已。
“那你来咸宜观,也是裴夫人授意的?”
“那倒不是,跟着裴夫人那个悍妇,只怕这辈子都没机会翻身了,还不如来道观活得自在,要不然,怎么能认识陈郎呢?”绿翘娇笑着,声音万种妖娆。
站在门外的鱼玄机再也忍不下去,终于狠狠一脚踢在门上,脱口骂道:“贱人!娼妇!”她这几年来悉心教导绿翘,就像温先生曾经教导她一样,什么事情都对她推心置腹,虽然名义上是主仆,其实如同姐妹,却不料,她竟是一直蒙在鼓里,一片真心付出,收到的竟是无情的背叛,她如何不恨?
门在里面插着,鱼玄机连推带踢,好半天才撞开。而陈韪见事情败露,忙不迭地爬起来抓了件衣服翻窗逃走了。
温庭筠赶到长安城时,便听到人们都在疯传“鱼玄机杀人入狱”的消息。大家众说纷纭,流传较广的说法是“鱼玄机将绿翘和陈韪捉奸在床,一怒之下失手杀了绿翘”。温庭筠震惊不已,赶紧去监狱走了一趟。几番打点,他终于见到了已经成为鱼玄机的鱼幼薇。她一身囚服,蓬头垢面,但是眉目之间秀美一如当年。
“飞卿,你终于来了。”她没有再称他“先生”,而是称了字,他们之间绵亘的距离,也似乎因这一句“飞卿”而缩短了不少,但也许,那只是一种错觉,现实的鸿沟,是永远无法跨越的。
“你这是何苦!”温庭筠终于忍不住泪洒胸前。“就算你做女冠,也不必和那些人混在一起啊!”
“不和他们混在一起,我拿什么来给母亲治病?”当初入咸宜观,鱼玄机母亲已经病重,贴出那张“鱼玄机诗文候教”的告示,其实最初的目的,是想赚钱为母亲治病。后来母亲去世,她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风流女冠,也就顺其自然了。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我不知道……”温庭筠闻言心痛不已。
“临死之前,还能见飞卿一面,玄机知足了。”
“你……真的杀了绿翘?”
“不然呢?让那个骗了我这么多年的贱人继续在我眼前惺惺作态吗?”
“幼薇,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想到子安他竟然……”
“飞卿,错不在你,没有李子安,还会有张子安、王子安。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这世间男子,有几个值得托付真心?”顿了顿,鱼玄机又道:“飞卿,如果我早生三十年,你,会娶我吗?”
温庭筠没有说话,心中只有无尽的痛。他想说“我会”,却动了动嘴唇,怎么也没能说出口。世俗的界限,他还是无法跨越。狱卒过来赶人了,温庭筠只好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其实在京城,打死侍女仆从的事时有发生,只要上下打点一番,基本就没什么事了。但偏偏审理鱼玄机一案的人,是被鱼玄机多次奚落的裴澄。裴澄求爱不得,偏偏鱼玄机执拗得很,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鱼玄机都不肯低头。审案时,她甚至话中有话地暗示道:“明公不要忘了,大中十二年,录取新科进士三十人,温先生与明公是同时进场的。”
这一句话彻底戳到了裴澄的痛处。当年温庭筠帮了七个人写文章,除了一人被发现,其他六人都顺利瞒天过海,而他,也是其中一个。鱼玄机讨厌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姓裴,更因为他的欺世盗名。
最后,裴澄判了她死刑。
囚车缓缓驶过闹市,人们或叹或骂,鱼玄机都充耳不闻。她知道温庭筠这些天必然四处奔走,希望能救她一命。但就算活下来,又能怎样呢?如果一个人执意求死,只怕没有人能救得,何况还有一个巴不得赶紧让她永远闭嘴的裴澄。
午时三刻,秋雨淅沥,片片黄叶被打落冰凉蚀骨的雨中。刽子手手起时,她听到有人远远地喊道:“蕙兰,我会!我会的……”那声音由远及近,虽然人声嘈杂,但她还是清晰地听到了。蕙兰,是十四岁那年他为她取的字。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鱼玄机嗫嚅着,缓缓吐出几句话,来不及说完,刽子手刀落,殷红的血将秋雨泼成无尽的凄凉。
人群散去,温庭筠手里捏着一颗骰子,站在凄怆的秋雨中,他的眼前,仿佛浮现了多年前的一幕,那个兰花一样的小女孩故意装着大人的样子说:“小女子何德何能,竟劳先生大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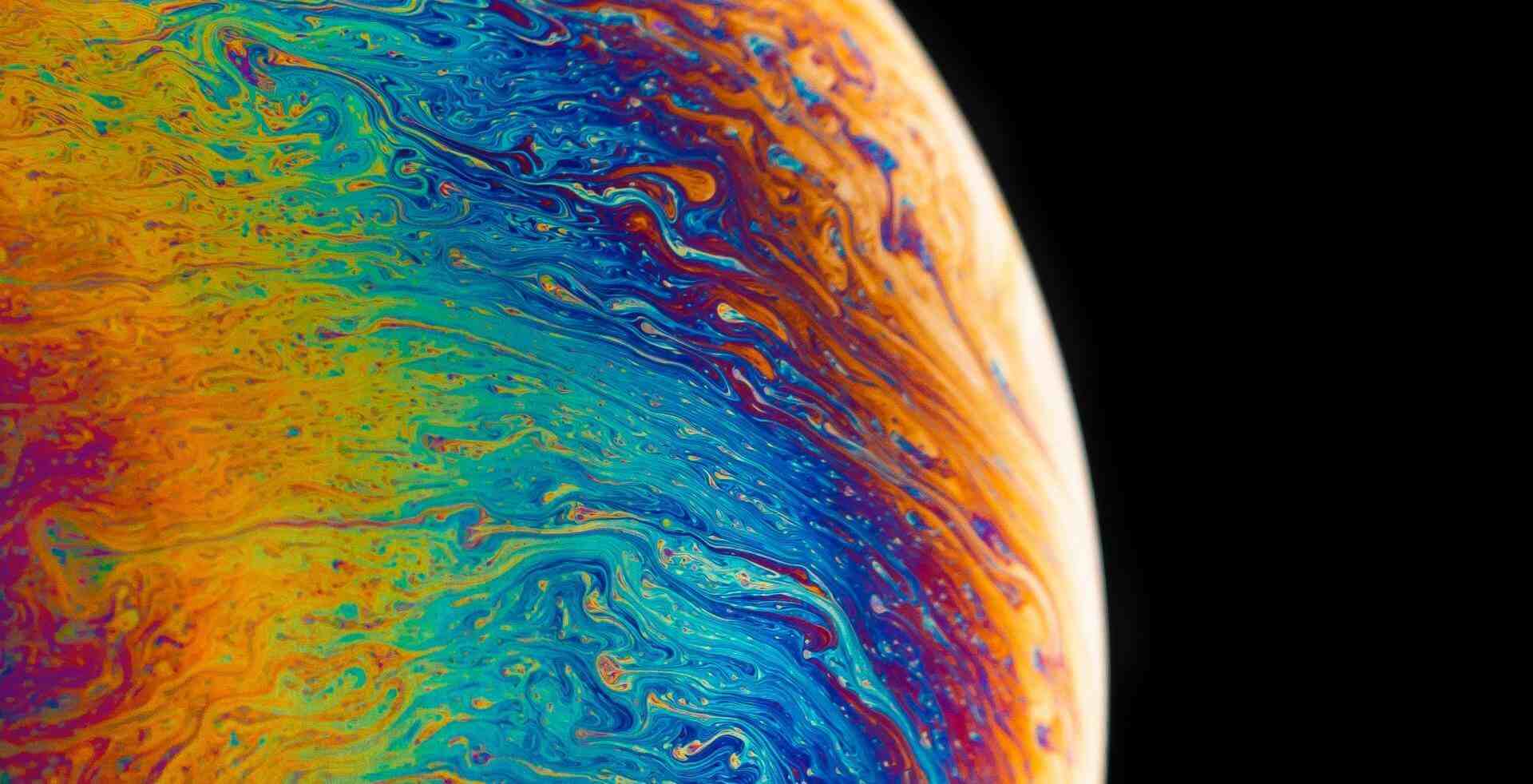
评论 (0)